威斯康星大学二校友:乔治·夏勒与造假大师易富贤之对比
去年下半年,我在出去旅游时碰到几位美国游客,为了锻炼自己蹩脚的英语,便跟他们东拉西扯地闲聊起来。闲话中,偶然提到乔治·夏勒博士(George Schaller),我说:他在做研究的时候是一位严肃的科学家,可当他提笔写作时,却成了一位忧郁的诗人 (He works as a scientist, but when he writes, he becomes a poet.)。听了我这句话,几名美国游客张大了嘴,作了一个夸张的惊讶表情,同时暗示自己没听说过夏勒博士。
也难怪夏勒博士在美国普通民众中知名度不高,在最近三十来年里,他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亚洲,尤其是青藏高原一带。可以说,如今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和一些主要物种能得到一定的保护,都跟他的研究与努力有着莫大的关系。如今老先生已经八十多岁,仍不顾高原环境恶劣,坚持到野外做研究。
从那次出游回到家中没几个月,夏勒博士的新书《第三极的馈赠》出版了,约略算来,这好像是他在中国出版的第6本科研和科普作品了吧,在主题上也多多少少跟以前的几本书有些联系。
但是,不同于前面几本的是,这本新书用更多的篇幅,更加详尽地介绍了他近二十几年在青藏-帕米尔高原一带的多次考察,从他为挽救藏羚羊而一次次远赴高寒无人区考察研究的羌塘之旅,到几度深入藏西南秘境圣地,以及为保护马可波罗盘羊和雪豹,不顾当地局势动荡,而造访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各国。
野外考察充满艰险,研究过程往往枯燥,夏勒博士及其团队经常需要测量和计数,每天都要撰写笔记,但这一切却是获得第一手资料,了解当地生态环境状况的必由之路。而这些考察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希望改善当地居民与大自然的关系,通过生态旅游之类可持续的方式,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在保护动物的同时,也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
凭借这样的研究,以及每天坚持不懈的笔记记录,夏勒博士在与各国研究者撰写出高质量的科研论文之后,还能通过他创作的一系列兼具科学性和趣味性的科普作品,向普通读者介绍他们的科考过程与结果,增强公众的环保意识。
在夏勒博士参与保护的物种之中,最著名的除了大熊猫,大概要算藏羚羊了。正是因为夏勒的野外考察,才发现了沙图什的血腥真相;正是因为他和同行们在亚洲和西方的不断努力,才使得沙图什贸易最终被禁;也正是因为他的研究和呼吁,唤醒了根植于藏人宗教意识中的护生观念。如此,藏羚羊的命运方才得以暂时扭转。
但他关心的不单单是这些大型旗舰动物,他也曾为青藏高原上一种长期受到误解的小动物而呐喊呼吁,那就是小小的鼠兔。在他涉足青藏高原之前,有相当一段时间,这种小动物都被一些部门当作导致草原退化的替罪羊,而遭到大规模毒杀。是夏勒博士发现了它们对高原生态系统的重要作用,竭力阻止这种屠杀。
在《第三极的馈赠》中,夏勒博士不仅以妙趣横生的文笔,讲述自己在青藏-帕米尔高原上的科考与研究,而且也在“野性难驯的博物学家”一章中,提到了自己早年的一些经历和趣事,例如他怎样在少年时代从“二战”后的德国来到美国,怎样以令人艳羡又令人发笑的方式,入读阿拉斯加大学,然后抓住一切机会发展自己对博物学的爱好,最终得以进入威斯康星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以及他随后在世界各地进行的各种具有开创性的研究。
说到这里,我倒是想起他在威斯康星大学的一个大名鼎鼎的校友易富贤,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后者一直是所谓的“反节育派”急先锋。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个都跟中国有着密切关系的校友,似乎却在朝着相反的方向努力:易富贤在努力让中国人多生孩子,而夏勒则在为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被不断增加的人口挤压破坏而发愁。
若干年前,在一次讲座结束后,有记者向夏勒提出一个与人口增长有关的问题,老先生说了一句在我看来既真诚又委婉的话,大意是,他相信中国人有智慧解决自己的人口问题。然而仅仅几年之后,中国政府不顾业已恶化的环境,在充斥着种种谎言与偏见的舆论造势中放宽了生育政策。
而在这些制造谎言、宣扬偏见的人当中,所谓的威斯康星大学“高级科学家”易富贤是最积极也最受海内外媒体追捧的一个。他曾在2013年推出一条轰动一时的新闻,预测中国到2050年将会出现“失独家庭上千万”,这条消息很快得到中国众多官媒网媒以及《纽约时报》等国际媒体的报道与转载。要等到4年多之后的2017年,才有人揭露,他居然是用一种非常低级的错误方法,炮制出这个惊天数据的(详见中国学者、《人口困局:中国能否承受人口之重》作者李尚勇的博文《“失独家庭上千万”是个低级错误》)。
其实,任何稍具学术素养的人,只要能抛开自己的偏见或先入之见,都不难从易富贤那些满篇满纸充斥堆砌着数字的文章中,发现可疑的地方,例如他很少说明自己那些数据的出处,也很少向读者交代自己的研究方法。对他来说,玩弄数据就如同变戏法,著书立说不过是玩文字游戏。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两个威斯康星大学的校友似乎体现了德国人和中国人对待学术研究的态度:一个为了寻找事实真相,不顾高龄和高寒,年复一年地到野外做严谨的科学研究;另一个则用满篇不靠谱的数字装饰自己那些靠不住的荒谬“理论”,为了造出惊人的数据,达到骇人的效果,甚至不惜玩弄低级骗术,造假撒谎,愚弄世人。
他们两人受到的不同关注程度,或许解释了中国为何至今难以跻身于世界科技大国的原因。
踏踏实实作研究的夏勒博士在媒体和公众中罕有人知,而一些学者的固执和政府的冥顽不灵,更是让他常常心生无奈,他在写到鼠兔的故事时发出的哀叹就是这种状况的真实写照:“然而很遗憾,对于科学证据,政府部门和普通大众往往是不理会、不关心,或根本无从了解。”
为保护各地环境,夏勒博士和研究团队常常根据自己科学研究,而向当地政府提出建议,只是后者往往对这些建议置若罔闻,就像他在“进入秘境圣地”一章的末尾所概括的那样:“遏制盗猎是我们提出的一条主要管理建议,但显然无人理会。至于在白马岗划分功能区,限定不同程度的开发利用,也许有关方面采纳了这一理念,但几乎没有实际的进展。”在受经济利益驱动的权力部门面前,科学不值一钱。只要这样的倾向依然存在,一些政府部门和官员就算把“科学发展观”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也依然是徒劳无益。
可是,在他的对面,造假撒谎的易富贤却名噪一时,不仅被众多媒体和公众奉为“高级科学家”,甚至有机会得到中国最高领导层的接见。无怪乎最近这些年“人口学”在中国成为“显学”:不光是易富贤这个妇产科专业的“科学家”,三教九流的反节育人士,都纷纷挤进这个领域,大放厥词,成为海内外媒体争相报道的“人口学家”。因为易富贤为他们指明了一条通往名利的捷径。而高层的加持,左右两派、国内国外媒体的共同吹捧与背书,还使得易富贤炮制的诸多荒唐的“学术成果”成为“颠扑不破”的谎言。
在《南方人物周刊》最近的一篇《二孩家庭进化论》中,记者虽然已不再提易富贤那个惊世骇俗的“失独家庭上千万”,但对他编造这一谎言的事实,却也三缄其口。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经济报告》在2017年第10期中,又把他那篇漏洞百出、充满假设的文章《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口》(例如他在分析“2008年之后活产数也存在大量水分”的原因时,说农村合作医疗的“人均补助标准由2008年的每人每年80元提高到2017年的450元,基层政府、医院、个人有强大的动力虚报分娩数”。但实际上这笔补助并不是直接以现金形式发放给农民,农民只有在生病就医后通过报销部分医疗费方式获得补助,而且合作医疗的个人缴费标准同样由起初的10元提高到180元,增长了十几倍,远远超过政府补助的增长幅度,农民若虚报新生儿数量,则家庭缴费增加,而套取的“福利”并不一定会增加多少。易文以此作为人口数据存在水分的原因,显然站不住脚)当作科学论文发表,同样对他造假一事绝口不提。毕竟投鼠忌器,要撬倒官方、媒体与民间共同塑造的这尊科学伪神,众多媒体就不得不反思甚至追究自己传播谎言的责任。易富贤的例子说明,“权力导致腐化,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化”的说法,不仅适用于传统权力,也适用于被称为“第四权力”的媒体势力。
中国未来的人口政策会走向何方?朝着威斯康星大学那位德裔校友希望的方向?还是朝着他那个华裔校友希望的方向?无论结果如何,受到影响的都不仅包括中国人,也包括中国的邻居们,以及一些更加遥远的国度及其野生动植物:为满足中国庞大人口对大豆的需求,亚马逊雨林成片倒下;为满足中国富豪无度的虚荣心和贪欲,非洲大象和犀牛而危在旦夕。
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因为罔顾科学的浮夸风,而给中国人造成巨大的灾难。明年就是“大跃进”开始60周年,但是通过威斯康星大学这两名校友一受冷遇一受追捧的不同境遇,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中国的决策者还是知识精英,以至于广大民众,都从未真正走出“浮夸风”的阴影。为了迎合领袖的意志,为了所谓的政治正确,一些所谓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不惜扭曲真相,编造谎言,欺世盗名。
也许,我们应该多读读夏勒博士的作品,看看一位真正的科学家如何作研究,如何作科普。别的不说,跟他那个校友那些满篇数字、满嘴跑马的作品相比,至少夏勒博士的书可读性更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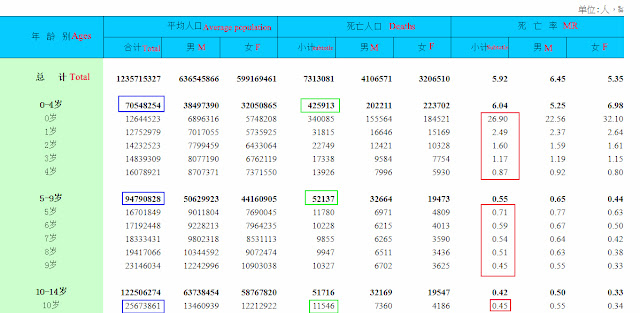


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