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什么被twitter噤声
8月的一天,当我登录twitter账号时,在页面上看到twitter留给我的消息,说我在〈纽约时报〉中文网这篇推文(https://twitter.com/nytchinese/status/1137585111497674752)后面的跟推里发表了“侮辱性”言论,要求我必须删除那条推文并通过手机验证,才给解推。当然那篇跟推现在已经被推特屏蔽了,不过我还大致记得自己在里面说了什么:我批评美国对“习瘟猪”太天真,因为“习瘟猪”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跟美国谈判,它只是想拖时间,拖到川普下台。诸如此类吧。
我不是第一次在推文中提到“习瘟猪”几个字,而且那篇推文是在我被锁推之前一两个月发的。估计是五毛狗和/或反节育派集中向推特检举了我的这一则推文。至于锁我账号的是推特机器人还是真人,我可说不准,因为机器人并不一定比真人更客观,真人也未必就比机器人更讲道理。
不过,这件事之所以发生在8月,可能另有原因。
在我账号被锁之前,我到藏区作了一次奇异的旅行,邀请我的是一位很久没有联系的熟人,他们家是父母辈移民新疆如今又离开新疆的汉人。当我要求与同行旅伴AA制旅途中的各种费用时,这位熟人说不用我掏钱。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
后来的经历证明,那是一次洗脑之旅。同行的另外3个旅伴一路上以各种方式向我灌输诸如“习总对藏人很好”、他上台后藏区发展很快以及维吾尔人是恐怖分子之类的观点。在我表达了不同的看法后,我也就成了他们排斥的对象。
有意思的是,我后来才发现,我们的这次旅行居然在当地宣传机构的“新闻”里跟习瘟猪的扶贫大业扯上了关系,虽然我可以肯定习瘟猪做的唯一事情,就是没有禁止活动的主办者做一些帮助藏人的事情。是的,你没有看错,在这个国家,党允许你做善事就是对你最大的恩典,不管是做善事的人,还是那些接受帮助的人,都应该对党对习瘟猪感恩戴德。当然,他们做的善事也要算作习瘟猪的“扶贫”功劳。
并非巧合的是,我们参加的那次活动,跟几乎同一时期一名美国外交官员被邀请到藏区参观的活动是同一类。
如果我没有猜错,可能是因为我一直在推特上批评反节育派的谎言,为计生政策说了几句公道话,因此共匪以为可以利用我来给习瘟猪拍马屁。
在他们的企图失败之后,我的账号也就遭到了攻击。当然也不排除反节育派也参与了这件事情。我相信反节育派对我的痛恨程度一点不亚于共匪对我的痛恨。而且五毛狗中本来就有不少反节育派,否则纽约时报之类的西媒怎么可能与坏球屎报在传播反节育谎言、发动反节育宣传方面如此亲密无间地合作呢。
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因为自己的网上言论被任何警察约谈。大概我的影响力还达不到被约谈的标准。
对反节育派来说,我被锁号是一大利好消息。这不〈华尔街日报〉不久前又发了一篇传播易富贤谎言的文章么。一开始,那篇文章的中文版是向读者免费开放阅读的,并且可以在后面匿名评论。接着,在我发出两条未必能够通过审查的评论后没过多久,读者就无法阅读那篇文章的全文,更无法评论了。
西方(至少是那些移民西方的华裔媒体人)是很尊重言论自由的,共匪也是同样。当然他们都对那些符合其立场的言论更尊重一些,至于那些不符合其立场的言论,他们都有办法让它们消失。
于是他们现在发现,言论自由已经不仅威胁到共匪的独裁专制,而且也对民主构成了威胁。不得不说,在渗透西方的过程中,这是共匪做得最成功的:它们终于成功地让西方人认识到言论自由的危害了。
我很高兴成为那个对他们双方都构成小小威胁的人。
过几天就要回我那已经或即将消失的故乡了。这一次,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平安归来。
我不打算向任何反共团体或民主自由派求助,共匪固然是到处搞强拆,那个自称“为穷人做事为富人说话的”的所谓“自由派”经济学家茅于轼和他在天则的那些狗屁专家们,还不是成天琢磨着怎么夺去农民的土地和房屋,把他们驱赶进鸽子笼一样的楼房,让他们像猪一样繁殖出低人权的人廉价劳动力,为资本家创造不断增长的利润。我早已看透了,他们中有相当多的人,跟共匪都不过是一丘之貉罢了。一群血管里流着狼血的人,天天在那里表演吐狼奶。
我不是第一次在推文中提到“习瘟猪”几个字,而且那篇推文是在我被锁推之前一两个月发的。估计是五毛狗和/或反节育派集中向推特检举了我的这一则推文。至于锁我账号的是推特机器人还是真人,我可说不准,因为机器人并不一定比真人更客观,真人也未必就比机器人更讲道理。
不过,这件事之所以发生在8月,可能另有原因。
在我账号被锁之前,我到藏区作了一次奇异的旅行,邀请我的是一位很久没有联系的熟人,他们家是父母辈移民新疆如今又离开新疆的汉人。当我要求与同行旅伴AA制旅途中的各种费用时,这位熟人说不用我掏钱。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
后来的经历证明,那是一次洗脑之旅。同行的另外3个旅伴一路上以各种方式向我灌输诸如“习总对藏人很好”、他上台后藏区发展很快以及维吾尔人是恐怖分子之类的观点。在我表达了不同的看法后,我也就成了他们排斥的对象。
有意思的是,我后来才发现,我们的这次旅行居然在当地宣传机构的“新闻”里跟习瘟猪的扶贫大业扯上了关系,虽然我可以肯定习瘟猪做的唯一事情,就是没有禁止活动的主办者做一些帮助藏人的事情。是的,你没有看错,在这个国家,党允许你做善事就是对你最大的恩典,不管是做善事的人,还是那些接受帮助的人,都应该对党对习瘟猪感恩戴德。当然,他们做的善事也要算作习瘟猪的“扶贫”功劳。
并非巧合的是,我们参加的那次活动,跟几乎同一时期一名美国外交官员被邀请到藏区参观的活动是同一类。
如果我没有猜错,可能是因为我一直在推特上批评反节育派的谎言,为计生政策说了几句公道话,因此共匪以为可以利用我来给习瘟猪拍马屁。
在他们的企图失败之后,我的账号也就遭到了攻击。当然也不排除反节育派也参与了这件事情。我相信反节育派对我的痛恨程度一点不亚于共匪对我的痛恨。而且五毛狗中本来就有不少反节育派,否则纽约时报之类的西媒怎么可能与坏球屎报在传播反节育谎言、发动反节育宣传方面如此亲密无间地合作呢。
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因为自己的网上言论被任何警察约谈。大概我的影响力还达不到被约谈的标准。
对反节育派来说,我被锁号是一大利好消息。这不〈华尔街日报〉不久前又发了一篇传播易富贤谎言的文章么。一开始,那篇文章的中文版是向读者免费开放阅读的,并且可以在后面匿名评论。接着,在我发出两条未必能够通过审查的评论后没过多久,读者就无法阅读那篇文章的全文,更无法评论了。
西方(至少是那些移民西方的华裔媒体人)是很尊重言论自由的,共匪也是同样。当然他们都对那些符合其立场的言论更尊重一些,至于那些不符合其立场的言论,他们都有办法让它们消失。
于是他们现在发现,言论自由已经不仅威胁到共匪的独裁专制,而且也对民主构成了威胁。不得不说,在渗透西方的过程中,这是共匪做得最成功的:它们终于成功地让西方人认识到言论自由的危害了。
我很高兴成为那个对他们双方都构成小小威胁的人。
过几天就要回我那已经或即将消失的故乡了。这一次,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平安归来。
我不打算向任何反共团体或民主自由派求助,共匪固然是到处搞强拆,那个自称“为穷人做事为富人说话的”的所谓“自由派”经济学家茅于轼和他在天则的那些狗屁专家们,还不是成天琢磨着怎么夺去农民的土地和房屋,把他们驱赶进鸽子笼一样的楼房,让他们像猪一样繁殖出低人权的人廉价劳动力,为资本家创造不断增长的利润。我早已看透了,他们中有相当多的人,跟共匪都不过是一丘之貉罢了。一群血管里流着狼血的人,天天在那里表演吐狼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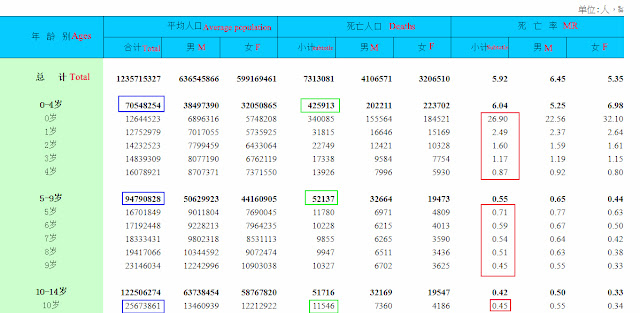


留言
張貼留言